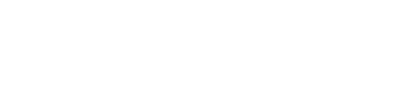


《奥利安娜》的编剧戴维·马梅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剧作家和导演,被誉为“21世纪初美国最好的戏剧作家和影视剧作家”。戴维·马梅特以其独特、强烈的"马梅特"语言风格自成一格,在话剧及电影领域都倍受推崇,自上世纪70年代戴维·马梅特凭借《鸭子变奏曲》和《芝加哥性堕落》等作品在美国戏剧界崭露头角以来,至今已创作了超过30部戏剧剧本作品,10多部电影剧本作品,屡获纽约戏剧评论奖、奥利弗戏剧奖、托尼最佳戏剧奖、普利策戏剧奖等戏剧奖项,还曾凭电影《旭日》和《汉尼拔》获得过奥斯卡奖的提名。
戴维·马梅特笔下的《奥利安娜》以"性骚扰"这样敏感的话题引发人们的关注,自问世以来始终是一部最具社会争议的剧作。《奥利安娜》是一部三幕剧,只有两个人物、一个场景,剧里展示了大学男教授约翰与大学女生卡萝尔在办公室的三次谈话,最终教授被指控性骚扰而近乎身败名裂。
本轮演出《奥利安娜》中的两位主人公教授“约翰”和大学女生“卡萝尔”的分别是周野芒和青年演员孙语涵。该剧将颠覆鼓楼西传统舞台的布局,呈现360°无死角的观剧体验。新京报记者对话《奥利安娜》剧本译者兼文学顾问、戏剧翻译家胡开奇,从剧作和译作角度揭秘了《奥利安娜》这部作品的看点和难点。

新京报:《奥利安娜》这部作品的语言特点是什么?
胡开奇:《奥利安娜》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马梅特作品,他为人们所注目的戏剧语言最突出的风格是短句和断句的对话,这种风格有来自品特和贝克特的影响,但马梅特的对话极具独特性,因而被称之为“马梅特语”。另外,马梅特剧作的戏剧语言的动作性很强,是一部好的剧作应该具备的特点。他的作品几乎没有舞台提示,完全依靠戏剧语言中的动作性和戏剧性,这也是他的剧作的戏剧艺术的高度。

新京报:您为什么要翻译《奥利安娜》这部作品?
胡开奇:马梅特作品的批判精神是美国典型的现实批判主义戏剧的代表,他作品中也具有那种很强烈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种风格,翻译马梅特的剧本很难,它的很多的短句、断句,在美国剧作家当中比较少见。如果说翻译英国剧作家麦克多纳有难度,是因为爱尔兰文化背景和语言所造成,我觉得马梅特是美国剧作家当中最难译的一位。
另外,在爱德华·阿尔比去世之后,马梅特无疑是美国严肃戏剧顶尖的领军人物,但是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他的戏剧集。《奥利安娜》是我从2010年以前就开始翻译的作品,最近也与出版社确定,计划年内将《奥利安娜》、《房产经纪》《影业商人》三部他最经典的作品做成一部戏剧集出版。
约翰教授(周野芒饰)。摄影:塔苏
新京报:《奥利安娜》这部作品充斥着大量的对白,您在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文字的语言将这些不太容易体现的语境与情绪逐一体现?
胡开奇:像《奥利安娜》剧本里有大段的对白,而且完全是美国的校园文化背景,作为译者在文本上该如何完成文化和文学的转换,这一点我是有特别考虑。

好在我对美国和中国的大学文化和背景都比较熟悉,这里边确实要做到美国社会文化抵达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转换。特别是对美国大学文化当中的很多术语,惯例与习俗的处理。必须考虑到中国大学的学术语言,中国大学的教授们会如何讲话,学生们又如何与教授进行交流,这当中确实存在一个文化上转换。作为此剧译者,要确实对美国大学文化和中国大学文化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一点上我还比较熟悉。
新京报:您作为一名资深翻译家,您在翻译《奥利安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的困难在哪里?
胡开奇:戏剧翻译很辛苦,甚至要比一般人想象还要艰难。对于我来说,我作为戏剧翻译家,必须考虑就是如何将一部西方剧作呈现于中国舞台,这是一个文化与文学和舞台的转换问题。
比如说,马梅特的作品美国地方风格很重。他作品里的很多双关语、断语,与其他英美剧作家相比,使用量非常大,这样就给戏剧译者造成了相当大的难度。他使用的这些断语,既非常具有生活化,也非常符合舞台的情境,作为译者,就必须把这些有效地串连起来,并转化成作为中国观众能够接受戏剧的情景和作品。
卡萝尔(孙语涵饰)。摄影:塔苏
新京报:回到舞台上,如果导演和演员遇到瓶颈的话,您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和启发?
胡开奇:我和周可导演合作多年,我们之间在创作上的很多想法都非常心有灵犀。
比如这次《奥利安娜》我们曾讨论关于结尾部分的处理。面对原先品特与马梅特对这部作品的结局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品特导演的伦敦版采用了马梅特最初的剑桥版结尾,而马梅特的纽约版与最初剑桥版的结尾则完全不同。我认为,马梅特的结尾呈现就是要揭示美国现代校园文化的“政治正确”,坚持这种“政治正确”实际上在目前美国校园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品特更着重于一种人性的呈现而更具偶然性或不确定性风格的结尾。纵观此剧情节的发展线,这个结尾的突兀与偶然,体现了一种现代性;而这个结尾的不确定性,又体现了一种后现代性。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周可的结局处理很好,她采取了一个我觉得是很具现代性的处理方式,设定了一个比较开放性的结局,把最终问题留给了观众,也很符合马梅特作品的气质。
《奥利安娜》剧照。摄影:塔苏
新京报:《奥利安娜》的故事尺度较大,您在翻译时如何处理?
胡开奇:关于“性骚扰”这个题材搬上当下的舞台并不是问题,我们应该看到马梅特的剧本性语言上尺度很大。我作为翻译者对于文学剧本,通常不作删节,但导演周可一定会有她自己的处理,而且我认为她必须有适宜中国舞台的相应处理。
这又要回到之前的问题,我们译者在翻译文本的整个过程中,从译者到导演到演员到舞美整个过程当中,必须想到的是最终它要在中国舞台上呈现,当它在中国舞台上展现的时候,必须考虑中国观众的接受程度。
新京报:对于这样大量对白组成的戏剧作品,创作者一旦稍有偏差就会将作品变得非常枯燥,从译者的角度您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胡开奇:牵涉到现代戏剧上,我们的译者就是要把一部西方文本完成它的一个文化和文学的转换,与整个创作团队结合,最后要呈现在舞台上的是一个中国舞台的《哥本哈根》或中国舞台的《奥利安娜》。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想不应该会有长篇枯燥无味,洋腔洋调的硬译过来的东西。
如果说戏剧译作更重要的是完成一个文化与文学转换的话,那么导演更重要的是完成它的舞台转换,如果这两种转换都结合好了,那么这个作品就在中国舞台上的呈现就不会有问题。至于我个人来说,多年来我的译剧观念来自现代戏剧翻译理论与个人译剧实践的结合。戏剧翻译就是要面对文化转换、文学转换和舞台转换这三大关,只有这样才算完成了一部戏剧翻译的过程。

《奥利安娜》剧照。摄影:塔苏
新京报:今年是鼓楼西剧场五周年,您对于这个剧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如今回顾五年前最开始决定做“直面戏剧”的时候,您达到自己的预期值了吗?
胡开奇:鼓楼西剧场和李羊朵五年来一路奋进,始终坚持着戏剧的哲理性、思辨性与文学性,在坚持走这条道路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当下还是非常需要人文戏剧的。
鼓楼西制作的《一句顶一万句》无疑为他们开拓了一条新路线“中国经典戏剧”,这种追求是非常可贵的。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坚持着西方当代经典的小剧场道路,这会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的发展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从《枕头人》《丽南山美人》《那年我学开车》《烟草花》到今天的《奥利安娜》一路走来,这些作品上演后所引起的反响,表明了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都揭示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并同时在揭示与反思人类的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在给人们一个启蒙,引导人类继续朝向最理想和正确的方向上走,我觉得这就是鼓楼西作为一个戏剧剧场的精神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