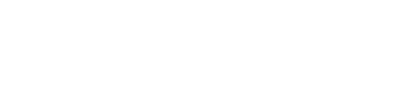


第章
捕捉:夜色
破旧的筒子楼里布满了爬山虎,草丛里蟋蟀叫着“唧唧,唧唧”。 大多数人已经睡着了。 昏暗的窗户点缀着夜色,蝰蛇蹲在角落里。 她抱着娃娃,蓬乱的发缝里有一双无力的眼睛凝视着灯光。 夜晚对她来说是一样的,那寂静和咯咯的笑声让她感到恐惧,她的身体不由得颤抖着
林溪的服装很干净,明亮地站在灯光下。 她眼前有一面镜子。 她在练习微笑。 眉心、嘴角、苹果肌、仪容和行动,甚至笑容的宽度。 她在各种场合练习最“完美”的表情。 她对于完美的要求,不允许有任何事故。 她在一份小报上写道:“出生以来,一切都需要练习。 我们一直在练习微笑。 我甚至记得看到三流作家说的“终于变成了不敢哭的人”。 笑着笑着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顺着睫毛从脸上滴下了眼泪。 泪水从苹果肌上蜿蜒而下。 她用指尖抚摸着眼泪,拿起纸巾的手势。 动作的幅度,精确到眼泪滴落的角度和感情。
她控制着自己的感情,让毛孔毛骨悚然。
第二天早上起床,林溪像往常一样起床做早饭。 两片面包,两片荷包蛋,两杯豆浆,都正好两个,不少。 蝈蝈的闹钟响了两次。 她黎明时终于沉沉睡去了。 时间已经八点了。 林溪不耐烦地拽着蝈蝈起床。 林溪把早餐塞进蝰蛇嘴里,蝰蛇忍不住恶心,骂他不听话,骂他和死去的父亲德行,把蝰蛇从地上捡起来丢下的煎鸡蛋放进嘴里。 她多次扬起袖子时,又白又软的手臂上有很多伤痕。 林溪拿着粉底涂在她的伤口上。 母女总是抱着书包出门。
学校教室里迎来了神秘的嘉宾,咚咚地在孩子们的掌声中走上了讲台。 课程的主题是“我的母亲”,孩子们大声描绘着自己的母亲。 只是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咚咚地抱着蝈蝈,让他讲和妈妈的故事。 蝰蛇忍住眼泪说:“妈妈是光,蝰蛇是光。”妈妈知道人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勉强活下去吗?”
彤彤在蝰蛇的身上再次闻到了她不到这个年龄的气味。 她抱着蝰蛇哭了。 她甚至无法想象一个7岁的女孩经历了什么。 她哭了。 蝈蝈还在用力地笑着。 她擦着蝈蝈身上粉底背后的秘密。 蝰蛇全身都受了伤。 蝰蛇警惕地涨得通红。 她的眼睛里弥漫着前所未有的恐惧和通红的脸。 每个人都不喜欢透露自己的伤疤,不会忘记伤害了自己。 如果我们自己变强了,就要学会忘记。 如果忘不了,只有努力毁灭它,才能结束一切。 ”
彤彤紧紧地拥抱着她的眼睛,泪水填满了她的眼睛。 她一字一句地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做了什么,所有他的妈妈都生病了,只让一个七岁的孩子承担了这个畸形长大的一切。 蝰蛇的语言和语境都不属于这个年龄,但她承担了不属于这个年龄的痛苦。 这个不到七岁的孩子在她怀里颤抖着身体,哭得通红。
彤洗了身体。 数百道令人毛骨悚然的伤口深深地渗入皮肤。 她问了一下发生了什么。 虾蛄摇了摇头,流下了眼泪。 存在于这个世界需要价值,做坏事就要付出代价。 伤口只是为了让自己记住发生了什么。 彤两个孩子被虐待后联系了保护组织。 因为彤不是监护人,所以委员会没有受理。 彤不是救命稻草。 彤不是救蝙蝠一命的稻草。 她甚至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意思,能穿得很暖,生命的火种是妈妈给的,这团火只能自己生,长大后面对这个丑陋的世界,至少给了她成长的机会。
在彤申所被林溪刑拘,所长以胡闹为由拒绝了她的申请。 下课后,她拉着棕榄走出校门。 林溪已经等校门了。 他已经等校门了。 顿了顿有点吃惊,打着简单的招呼。 棕榄的脸犹豫了一下。 她放开咚咚的手,脸上浮现出标志性的笑容,扑到林溪的怀里。
“你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 ”彤彤叫住了人群中的林溪。 林溪嗤之以鼻,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因为没有被爱过,所以不能太爱别人。”
“爱是温暖的! ”彤彤拼命解释,看着蝰蛇,她最终选择了欲言又止的沉默。
林溪说:“很奇怪。 他轻蔑地说:“躲在冰冷的钢筋混凝土中,寻求温暖。”
她压住怒火看着林溪母女消失在人群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弥漫了她的全身,她感到莫名的无力感。
彤茫然失措地回到了家。 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蹲在她的门口。 男孩身体也瘦了,脸也憔悴了。 彤想起他是肇事司机周寒的儿子,就叫周粥。 今年应该在报考高中。 之前在病房见过一次,和上次见面时完全是另一个人。 他已经好几天没睡好了。 彤彤带他去了麦当劳,看着他狼吞虎咽地把汉堡塞进嘴里,一边吃一边眼里的泪水在往下滴,彤彤让他先吃点东西,有什么话慢慢说。
李先生到达花溪村时,太阳已经升起,村口有几个老人坐在小卖部门前,正在田里抽烟打牌。 他下车问村里有没有林姓的房子。 一个老人咂了咂剩下的两颗黄牙,摇了摇头说自己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从来没有问过村子里什么时候来过林姓。 这个村子是个老村子,只有花姓的家人。 老人用自己的门牙发誓村子里没有异姓
开了一夜车,小李不顾疲劳,从手机里拿出林溪的照片,问有没有人见过她。 几个老人热情地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手机,脑袋瓜快碎了也没什么印象。 小李失落的感慨这次好像失效了。 一位老人凝视着林溪的照片,犹豫地摇了摇头,呆呆地说。 "这姑娘简直就像个花汉. "
“花汉儿是谁? ”李追着问。
老人认真地解释说:“花汉儿是花汉儿哦! 花溪村的男人都叫花汉儿。 ”
老人说:“你烦了吗? 我不清楚我在说哪个。 你的头套坏了啊。 ”。
小李不想和他争论脑袋瓜的事,听着听着,心烦意乱地问:“花汉儿现在在哪里?”
“死了。 死了二十多年。 撇下寡妇和孩子,真可怜……”老人指着村口的废墟。
李一顺顺着老人的手指方向找去,但墙壁残破的篱笆里只有瓦砾,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他在废墟里找了一会儿。 呆呆地凝视着阴沉的天空。 背着行李箱走来的两位中年女性在讨论着。 广播里说了今天会下雨。 一个女人看到一张陌生的脸,感到怀疑。 “你是哪一个? 你在这里做什么? ”
小李从废墟里出来,“这房子去哪儿了? ”。
小李拿出手机,找了一张林溪的照片给她看。 女子看着手机,惊喜地拍下了这条大腿。 小李高兴地看着她,“你认识她吧? ”我伸长了脖子问。
女人的兴奋无法用语言表达,挥手说:“你这个手机是最新的啊。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这是……"
李一的脸很快又沉了下去。 他的脸比嵌入天空的乌云还黑。 暴雨临近,雨丝落在泥泞的路上。 他只好暂时躲进邻居家避雨。 女人的丈夫曾坐在屋檐下。 村里的人都叫他柱子。 脸是黑色的,白眼看着妻子带着陌生人进来,冷冷地问道:“你在做什么?” 李一解释来的瞬间一愣,马上笑眯眯的,等不及直接敬礼,热情地把李一迎进屋里。 吃饭一会儿,暴雨就没停。 男子热情地邀请李一吃饭,停下了脚步。 掏鼻屎的手一直很闲,抱着肩膀和李一说话,挥手往杯子里倒酒。
小李到处跑,伺机离开村子,但男子已经光着脚出去叫花村长了。 我想向男人表明下雨天路滑,但还没开口。 村长的脚趾夹着热情的鞋,手里拿着鞋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 隔着墙说:“领导好! ”听到了。 的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