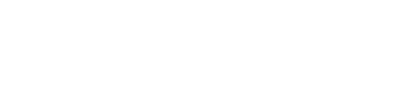



我和南翊自小青梅竹马,我喜欢他多年,然而他对我向来冷淡。
自幼被养在外府的妹妹回府后不小心快要摔倒在我面前那次,南翊稳稳地接住了她。
转过脸面向我时目光清冷。
「斗胆劝小姐一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便好,万不可痴心妄想。」
从此我藏起了自己的心事。
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南翊居然对我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原谅我可好?」
可我不愿,我不愿要这迟来的深情。
一
我和顾清柔同父异母,皆为顾府的女儿。
只是,因她母亲是被父亲从青楼里接回来的,被一向注重家风的祖父明令禁止,不得踏进顾府一步。因此,顾清柔与母亲一直住在外府。
直到我十五岁时,祖父逝世,父亲以参加葬礼为由接了她们母女回府。
那日,只一辆红木车马悄悄去了小门,从此,府上便多了两个人。
次日,父亲亲自领了她们母女去拜见了祖母,往日威严肃穆的脸上难得挂了柔和的笑。
「娴儿,过来见过你姐姐。」
我不愿,执拗地站在原地。
一个穿着白色绸缎的少女,盈盈走到我面前,乖巧地行了个大礼。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顾清柔。
不得不说,是个绝对的美人胚子。
一颦一笑,既有江南女子的温婉,又不失端庄与大气。
但令我真正意外的是,一个自幼养在外府的女子,一举一动,都是标准的嫡女之仪。
我将余光瞥向一旁那个威严的身影,心中嗤笑。
父亲大人倒是费心了。
将顾清柔藏于外府十余年,表面不提,暗地里却是没少花心思教导。
再看那外室,她仍低垂着头,谦卑有礼地站着,显得与世无争。
但她一定是有手段的,否则这么多年来凭什么抓住父亲。
母亲看不下去,推了我一把。
心想不能让母亲丢了面子。
我面上笑得亲切,上前搭上了她的手臂。
「姐姐辛苦了,这么些年在外府委屈姐姐了。」我假装伤心,不动声色加重了手上的力度。
她明显有备而来,丝毫不显惊愕与慌乱,端着那清丽明媚的笑容。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垂目道:「妹妹过奖了,姐姐在外府怎比得过妹妹万分之一。」
虽只是一瞬,但我却看到了父亲眼中的愧疚,也看到了顾清柔眼底藏起来的羡慕与不甘。
父亲在愧疚什么,她一个外室之女整天锦衣玉食,又在不甘什么。
我表情未改,松了手退到母亲身边。
告别祖母后,父亲特意唤我到她身旁,别有深意地说了句:「你姐姐不曾入府,往后你多多让她。」
我鼻尖微酸,低头应承了一声,快步走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同顾清柔交锋,让我知道了她在父亲心中的地位。
二
六月初八是京都各官宦小姐组成的诗会,由丞相之女为首,无柬不得入。
父亲自然是知晓此事,一大早就将我叫去耳提面命,无非是想让顾清柔尽早融入圈子。
我本想悄悄离去,不巧遇到了早在大门内等候的顾清柔。
「父亲让我同妹妹一道。」这话轻轻柔柔,却听得我极刺耳。
「嗯。」早被母亲三令五申不得与顾清柔作对,只得偷偷送了她一句国粹。
毫无意外,顾清柔在诗会上大放异彩,赢得各家小姐的欣赏,当然也因此树了不少敌。
「这是刚从父亲那得了的顶好的珠子,妹妹看是否喜欢,当是感谢妹妹。」
口不对心的家伙,听得我一身鸡皮疙瘩。
本想敷衍一句离开,可当看到锦盒里的东西时,心不由得一沉。
那是母亲嫁妆里的珠子,是外祖父为母亲寻来的,母亲一直舍不得带。
我豆蔻之年被母亲打扮一番,戴过一两次,被父亲评以骄奢,自从未曾佩戴过。
这骄奢的东西父亲倒是眼不眨就给了顾清柔。
我胸口一窒,猛地生出几分烦躁。
见顾清柔正挑衅地看着我,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准备离开。
她却突然晃了晃,身子朝我倒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闪避了。
眼看着顾清柔就要倒地,一个紫色的身影出现,稳稳地接住了她。
南翊逆光站在亭廊前,紫色的衣摆扫过廊中的落叶,顾清柔在他怀里,神情娇羞。
两人视线交融,旁若无人,好一个英雄救美。
一阵风拂过堂中桃李,明明沁人心脾,我却感到丝丝苦意。
南翊是侯府世子,我们自小在一个学堂,直至我及笄,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可我第一次见他面露关怀,却不是对我。
相识多年,他一直对我疏远,说男女有别。
他扶着顾清柔,目光触及我,又变得清冷。
「怎么回事?」他声音很轻,质问的语气却字字戳我心窝。
「风吹的。」我心中落寞,偏改不了面上的骄傲逞强,况且这本来也是实话。
南翊皱了皱眉,声音又冷了几分,他看了看顾清柔,转头看着我说:「斗胆劝小姐一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便好,万不可痴心妄想。」
我顿时僵住,心中有股难言的疼痛,什么叫万不可痴心妄想。
难道他一直以来都知道我的心意,才对我如此冷漠疏远?
痴心妄想?他有什么是我配不上的?
待我回过神来,他们已不知去向。
我压下心中难以言表的不适,拖着疲惫的身子上了马车。
我靠在车壁假寐,恍惚想起许多年前因自己字迹潦草,被老师罚抄诗。
我一直在学堂抄诗,南翊一直在学堂练字,我准备离开时他开始收东西。
我起了逗弄他的心思,便问:「你是在等我吗?」我歪头盯着他的眼睛。
「没有。」他的声音依旧是轻轻的。
「哦。」可他分明红了脸。
但这一次交锋,让我知道南翊心中没有我。
三
自那日后,南翊和顾清柔不时往来,赏花、下棋、谈诗……
明明我与顾清柔住处隔了十万八千里,却仍时常听见琴瑟和鸣,曲音婉转,似是互诉衷肠。
我仍记得,幼时我听南翊抚琴,便极喜爱。
但南翊喜武,对文人雅士干的事情是避恐不及,因此我很少能看到他抚琴,如今……
很快到了顾清柔的生辰,父亲大办,踌躇交错,歌舞升平。
可我根本无心观赏。
南翊现下正和顾清柔坐在一处,他二人不时低头耳语,看起来极为亲近。
有好友前来敬酒,顾清柔莞尔一笑,抓起酒杯正要饮,南翊忽然抓住她的手,将她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他皱着眉,眼里满是责备,南翊嘴唇翕动,顾清柔不时点头,小鸟依人般轻靠着南翊。
他竟如此赤裸地袒护她。
宴中,我喝了不少酒,看着南翊与顾清柔的身影,只觉得心烦意乱。
便带着丫鬟小桃去了后院,打算吹吹风。
却不料顾清柔竟跟了上来,你把南翊让给我吧。”
我望着她,我靠着树,挑了挑眉:「不可能。」
顾清柔一步步靠近,贴着我的耳朵,声音冰冷刺骨:「可你都配不上南翊。」
「你凭什么说……」
话未说完,顾清柔又倒了,亭廊的转角处人影晃动,南翊如离弦的箭一般冲了过来。
我了然,心中一片冰凉,竟生生散了几分醉意。
她是故意的,每一次都用这种破招,偏偏南翊吃这一套。
小桃看着我,支支吾吾:「小姐……」
我压下心中难以言表的不适,打断了她未说完的话:「走吧。」
「去哪?」南翊眼中藏着好些厌恶,似乎在讽刺着我:「你推了阿柔还打算一走了之吗?」
阿柔?呵!!!这称呼真亲近。
「没事的,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顾清柔脸埋进南翊怀里,轻声啜泣。
南翊一直皱眉看我,仿佛我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却仍不知悔改。
他的神情刺痛了我,我张了张口,想要解释,他却比我先开口:「二小姐同我情分生疏,往后不必再说些让阿柔误会的话,也不要再找阿柔的麻烦,劝二小姐一句,不要动不该有的心思。」
他说罢,抱着顾清柔离去,决然的样子堵住了我的欲言又止。
「他就在在意她至此吗?」我笑容苦涩,轻声问喃着,不知道是在问谁。
一阵风吹来,吹落了眼中翻涌的泪水。
我无力地闭了闭眼,这下,我与南翊多年的情分彻底是断了。
回去的路上,我又想起顾清柔说把南翊让给她,可我从未拥有过呀。
我心中沉积郁闷,感觉有一双无形的手慢慢地将我推离南翊,我与南翊,这辈子,许是不可能了……
这个生辰,是否如了顾清柔的愿?
两月后,我的生辰,应该许个什么愿呢?
四
此后,顾清柔更是整日与南翊腻在一处,我学会了视而不见,将心思藏起。
六月十五,母亲带着我与顾清柔到城外寺里烧香祈祷。
还是老陈的套路,到了山脚时几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与我们的护卫厮杀起来。
我偷偷掀开车帘,不料被一个模样凶横的人盯上,或者说他一直都在寻找我。
长剑如破竹之势向我刺来,我一时慌了神,忘了闪躲。
危急之时,小桃护了我,将我拥住,剑直直地刺向了她,血溅了我一身。
护卫将杀手解决,弃了马车,将我拽上他的马狂奔。
杀手尽量脱身朝向我们,此刻已非常明确,那些杀手确是为杀我而来。
突然几根针射进马臀,马受了惊,横冲直撞起来,完全不受控制。
护卫环住我紧紧地拉着缰绳,企图控制马不再发疯。
忽而一根长箭刺入了护卫的右肩,血不受控制地往外涌,瞬间染红了我的衣服。
「小姐,不怕。」他明显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我察觉到冷意,打了个寒颤,竟觉得肩头发麻。
「我不怕。」我尽量认真哭腔,身体仍不受控制地抖。
我们还是摔下了马,他拿身子垫着,我没有受伤。
他们还是追了上来,那些人骑在马上,将我们团团围住。
他面前挥舞着剑和刀,一下一下地落到护卫的手臂上、肩膀上、背脊上·······护卫没有放开我,他用身体为我铸成了铠甲。
只听见一道利剑划破空气,射进皮肉的声音。
温热的液体一滴一滴落在我的脸上。
他们杀了护卫,当着我的面杀了护卫,那个自我十岁起就跟着我的护卫。
我红着眼,拿起护卫的剑发疯似地砍向他们,剑被打落。
我颤抖着起身,用尽全身力气朝护卫爬过去。
我被打晕了。
梦里火光冲天,老弱妇孺皆被杀害,我想冲上去,却动不了,我想喊救命,却发不了声。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我面前倒下,无力感遍满全身。
突然一个面目狰狞的人提着刚砍下的头,一步步向我走来。
我害怕,无助。
那人提起刀欲将我的头砍下时,一个身影冲了过来,刀稳稳地落在他的右肩。
护卫挡住了我的视线,那人倒了,死了。
护卫也倒了。
我想冲过去,过去看看他,但是我动不了。
我挣扎着,无声地呐喊着。
护卫强撑着爬了过来,跪在我面前,他说:「小姐,不怕。」
他笑得很好看,眼中柔光竟能盖过身后的疮痍,我眼中蓄满了泪花,背脊却发麻,扯动心脏跳动的速度。我想回应他,告诉他:「我不怕,我不怕。」
他去了,梦也醒了。
醒来时我已在府中,母亲说杀手想将我转移,碰巧被官府巡城的人发现了踪迹,将我解救;母亲说我昏迷期间官府已结案,是父亲同意的。
几个训练有素的杀手是区区几个官兵就能撂倒的?他们穷追猛打却不杀我是为什么?为什么只针对我一人?
但父亲同意结案,一切尽显。
养病期间南翊不时来探望,眼底是我看不清的深情,我也不想看清了。
南翊来时,顾清柔总跟着。
我以静心养伤为由推了所有的探望,连南翊也不可以。
我又做噩梦了,梦里全时,我哭着,喊着,手胡乱抓着,有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
我醒了。
南翊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不发一言,就这样握着。
温热干燥的手包裹着我手,不知怎地,想起梦里护卫也是这样安慰我,忽然就很想哭。
南翊不知所措,笨拙地安慰我:「别哭,别哭。」
我发起了高烧,不久便昏睡过去了。
五
一连昏睡五天,中间偶尔迷迷糊糊地醒来。
第六天我已能进食,母亲说:「谢天谢地,你要是再不醒来,我便跟着你去了。」
我安慰母亲:「一个小风寒,倒让母亲如此担心了,是女儿的不是。」
「要真只是个风寒就好了,心病还须心药医。」我怔住,真不愧是我母亲。
第四天傍晚,南翊来了。
我正坐在院中发呆,一阵暖意袭来,才发现南翊把狐裘披在我身上,然后规规矩矩地系了个·········蝴蝶结。
「你···········」
「我扶你回去。」他不由分说扶上我的手臂,动作轻柔地不像他。
「我已向你父亲秉明,娶你为妻。」周围突然安静得可怕。
我没有说话,细细地看着他,白皙的脸上是一对剑眉星目,细看便是飞斜入鬓的眉衬上清水样的眼,常年练武,身上总有一股刚毅之气,是我曾喜欢的样子。
「你可愿?」见我不语,他忍不住问。
「不愿。」
「为何?」他急于想知道原因,打翻了桌上的茶盅。
「我想嫁时你不娶,现在我不愿了。」我淡淡地说,内心不曾泛起波澜。
南翊眸色一暗:「你可是在怨我?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原谅我可好?」
「你我不曾有过什么,何来原谅一说。」
南翊望着我的脸,喉间发紧:「可我是有苦衷的,我········」
「可我不想听了。」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无情打断。
南翊怔了好一会儿,呢喃了一句,只不过刚出口就消散在寂静中。
长夜如水。
风穿过窗隙吹动杏色的床幔,炭盆中点点星火残留着余温。
我辗转反侧。
夜晚最容易撩动心弦。
那护卫是父亲派来保护我的,或者说是来监视我的,我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的口传到父亲的耳朵里。我不喜欢这种行为,因此也一直对他不喜,他也不在乎我喜不喜。
开始时我一直斥责他,他却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
一来二去,我也就习惯了,也想通了,换了他还会有别人来。
他从来都是恪尽职守,中规中矩,不苟言笑。真的,我从没见过他笑。
我对他的印象仅停留于:我被罚跪祠堂,他在旁边站着;我上下学堂,他跟着;我与小桃嬉笑打闹时,他看着···········
他从来都是默默的,却无处不在。
夜晚格外的冷,喉间涌上一股咸腥,唇畔血腥萦绕,有些呛人。
果然有些人失去了才会开始想念,可笑也可悲。
六
这日早膳,家人齐聚。
桌上静默无声,唯有碗筷的碰撞声。
那外室也上了桌,给父亲布着菜,尽足了为人妻的本分。这时,父亲放下筷子,转动着手上的扳指:「我已同意轻柔与南翊联姻,过完年便交换庚帖。」
我神情冷漠,犹如看客。
回房的路上,我不发一言。
母亲只当我伤心难过,放慢了脚步与我闲逛起来:「别太在意,他不值得,母亲也不想你卷入权利中,沦为棋子。」
我停下脚步:「母亲,我想一辈子只当你的女儿。」
闻言,母亲神色一怔,显然是听出来话的不对劲。
母亲直直地望着我的眼睛:「母亲会护着你的,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我心一窒,涌上不能宣之于口的感动。
当晚,父亲来了我的院子。
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姐姐自小不在府内,比不得你,寻得个知心人不容易,你不要怨她!」
我没有理会父亲,只是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
我其实想问问,为什么父亲对我们的差别这么大,但我知道,就算问了,也只能得到一句不懂事的斥责。
见我不语,父亲语气不悦:「你如此这般,可是在怨为父?」
「母亲会一直是妻吗?」父亲一愣,显示没预料到话题走向。
「会。」也是,母亲有外祖父和舅舅们庇护,母亲会一直平安的。
次年三月,顾清柔与南翊交换庚帖,同年十二月,二人完婚。
二人完婚那天,我呆坐在窗前,喃喃道:「今年,何时会下雪呢?」
来侍候我用药的婢女说:「京城的雪可不是年年都下,倒是边疆,听闻年年都下,茫茫一片,漂亮极了。」
护卫也曾说过边疆的雪漂亮极了。
婢女一边添炭,一边絮絮叨叨的。
「奴婢也想看雪,好多好多雪。」
「幸好京城不常年下雪,不然您冬日可就难捱了。」自从那次寺庙之行被刺杀后,我就落下来病根,不外乎婢女会这么说。许是生了病,人也跟着金贵起来。
不过是吹了一点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呀!小姐,你怎么哭了·········」
后来她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那天的梦里,有漫天飘洒的大雪,还有我的少年郎。
梦醒后,身边空无一人。
呆坐了片刻,起身,收拾行囊。
离开之前,看着台案上的笔墨纸砚,留了句话:「边疆有京城没有的大雪,我想去看看。」
同年十二月,一人一马离京而去。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