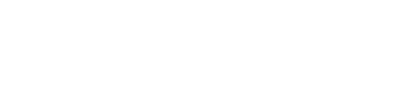


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杰出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知识产权法学学科的奠基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教育的开拓者,知识产权法学中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国际著名知识产权学者,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教授赴美参加学术活动期间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北京时间2023年3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享年75岁。
讣告全文:

此前报道:
刘春田:书山千度春 学海万般田
幼随父母从老家山东乐陵来到北京,知天命之年还说自己是典型的山东人;受几代人熏陶,酷爱京剧,十岁时,为全家人能听上马连良的《朱砂井》,不惜“立雪”广和剧场,彻夜排队。在哥哥的诱导下还差点进了中国戏曲学校;在学术问题上,真诚地与人辩论,但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
刘春田教授给人留下的是一种线条硬朗、观点犀利的印象。这种印象,即便不眼见其人,一个熟稔的画师也能勾勒出其风骨神韵。
刘教授热情地与记者握手寒暄。他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握手时很有力度。这是一副标准的山东大汉形象。刘教授告诉我们,山东人率真,为人直率、真诚,当然也比较喜欢较真儿;而北京呢,多元文化的融会,肥田沃土,养育长材大器,形成了北京人大度、豁达,兼容并包的品格。家庭的耳熏目染培育了他山东人的性情,而五十年的北京生活,则让他涵蕴了京腔京韵。
更有意思的是,刘教授突然话锋一转说,世界各国的法律既有差异性,也有共通性,在相互借鉴交融的同时又不失其本真,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青春无悔
人类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有高潮,也有低谷。高潮时要懂得居安思危;低谷时也应坚守信念,不可随波逐流。有一段岁月,把所有中国人都卷入了史无前例的动荡。在那段时光中,刘教授两次与大学失之交臂,提起那段经历,他仍然唏嘘不已。他说他们这代人,经过了太多的史无前例,不过他相信这些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1966年,刘春田高中毕业。清华大学招生,素有“找生”的传统。他们利用校庆,把北京几所重点中学的应届毕业生接到清华园,参观学校、介绍专业,鼓励报考。
他和不少同学一样,瞄上了各自钟爱的专业。6月,距高考只剩下一个月。若按惯例,不出意外,他们再有两个半月就进入大学。不料,十年“文革”开始,他第一次与大学擦肩而过。
1968年,刘春田赴山西晋北插队,开始了直面人生的漫长岁月。1970年,他到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因工作出色,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入学考试,专业是仪表自动控制。那年入学机制已由原来的推荐入学改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
他们单位只有一个指标,和他同考的是两个小学未毕业的学徒工。于是,涉世未深的刘春田信心满满,自认为是不二人选。但考前,有人告诉他:“你何必白费功夫,早就内定了!”刘春田颇不以为意,开玩笑地说,他们认字么,恐怕连教室也找不到!不料,那位小学生幸运地上了大学。造化弄人,刘春田再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时代可以轻易地改变人的命运,却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天性。厄运有时可以将人彻底击溃。但年轻的刘春田天性达观,他认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可以点石成金,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他认为,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把《论语》《孙子兵法》抄下来,朗读、体悟,还托人在太原图书馆借来《史记》《资治通鉴》等,整本整本地抄写,既学了历史知识,又练了字。此外,凡是能够借到的哲学和文学名著,也都一一涉猎。
刘教授笑言,那时他们单位宿舍里就一张桌子、一盏台灯,别人下班后都搓麻将、打扑克,惟有他“霸占”着桌子和台灯,读书自乐。
“古人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从小养成的读书与思考的习惯,让我的生活充实,只要有书看,便不觉苦,更谈不上寂寞,没有人可以荒废你,能荒废你的,只有你自己。上大学固然好,不上大学也不可自弃。对于我来讲,所谓十年“虚度”是形式上的,那时,我还是认真读了点书的。在工厂,无论领导、群众、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遇有难解或争议之事,往往找我寻求答案。能答则答,不会的就迫使你学,久而久之,我在工厂里有了个雅号"教授",刘教授感慨道。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当另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命运的转机
恢复高考,国家又获得了一次生机。1978年,刘春田按照招生简章,依次从高至低填报了八所学校。而在当时,人民大学排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前,位居招生简章的第一名,从此,他与人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教授对他的人生总结是,曲折而简单。曲折是因十年动乱遭受数次挫折;简单则是因除了当过十年的农民和工人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
自幼受家风熏陶,动荡时期又以读书为乐,刘春田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高考时,第一志愿是历史学。不料,鬼使神差地学了法律专业。多年后,他才知道,当时分管招生的系主任张希坡教授看档案时相中了他,把他偷偷地调到了法学专业。
刘教授戏称是张希坡先生的上帝之手将他带入了法学之门。然而真正带他登堂入室、走到今天的,是他的研究生导师佟柔先生。
刘教授回忆当年的读书生活说,当时授课的几乎皆为名师,如孙国华先生教法理学,许崇德先生教宪法学,高铭暄先生教刑法总论,王作富先生教刑法分则,江伟先生教民事诉讼法,佟柔先生教民法等等。诸多名师,各有千秋,但听来听去,惟对民法情有独钟。
当时同学多认为民法太复杂,十几人报考研究生,只有刘春田一人选民法专业。从此入室佟柔教授门下。
谈起佟柔教授,刘春田景仰之余,无限感念恩师。佟先生的敬业精神、学术造诣、治学态度和为人师表的杰出风范,至今仍铭刻在心中。
1985年,刘春田毕业留校。没有讲课经验,佟老师就为他创造机会,派他给某省县委书记培训班讲课。刘春田担心能否胜任,佟老师鼓励他说:“我看你行,去了出一身汗就过关了。”
刘春田硬着头皮登上了讲台,正值酷暑,加上紧张,三个电扇对着他吹,还大汗淋漓,全身都湿透了。一个上午过去了,刘春田恍然大悟:“原来课就是这么讲的啊!”
刘教授说,佟老师是一位伟人,他的敬业精神,堪称典范,非常人所及。学术是他生命的全部,上下求索、参悟天道与追求人格的至正至善,是他一生的写照。佟老师一生淡泊名利,他把学术思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他的学生乃至同行都衷心地尊敬他、爱戴他。
佟柔先生的人格魅力不断激励着刘春田,这使他成长为了一位著名的民法学者。刘教授认为导师佟柔对自己的影响至深。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当大哲笛卡尔下这个论断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把人作为一种考量世界的尺度,把人类知识的来源奠定在“我思”的基础之上,把人类的理智当成了事物的立法者。
对于一名学者来说,贡献思想则是证立自身价值的方式。在知识产权学界,刘春田的思想常常与众不同,他的观点,尤其引人关注。对此,他解释说,长期以来,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基本的理论问题,求新不是目的,而是源于对实践问题的困惑。没有人没有困惑,为了解惑,不得不反思传统的学说与理论,进而在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上,慎重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凡是认真思考的观点,即使与传统不合,也无所顾忌地提出,面对批评意见,他泰然自若。
“实事求是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学术求真,科学的生命在于批判与革命。在学术问题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天经地义的。思想和表达是每一个人的权利,真的学术,无关个人恩怨与得失。岂能看人脸色,因他人毁誉臧否而轻言放弃。”刘教授这样说。
当提到他的老朋友、已故学者郑成思教授的时候,刘教授凝重而坦然。他说,“郑老师是一位益友、良师。他是一位非常敬业、非常刻苦的学者,他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感念郑老师多年来的助益,同时坦承与郑老师的学术观点“每每不同”。“我们以诤友相识,长期合作,在诸多问题上相互辩难,争了二十多年。但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在他去世前,我们还在讨论问题,还就信息产权问题各抒己见。”
当记者追问二人的论战有无结果时,刘教授的回答质朴而果决:“我们俩人对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执著,谁也说服不了谁。我的观点是思索的结果,我相信这些观点终究会由实践作出回答,如果合于科学,总会被人接受。”刘教授分析说,他也反思过二人的分野,根本原因或许还在于各自知识结构的不同。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刘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代。几百年来因应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时俱进。工业革命时代的资本主义是“创”“造”兼备,后来由于科学技术与市场化的提高,“创”“造”分离,把“创”留给了自己,把“造”则甩给了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国正值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又遭遇了“网络时代”这样一个人类崭新生产方式的来临。中国当前的长处是“造”而不是“创”,我们面临的是工业化与网络化毕其功于一役的重大变局。与其他国家一样,知识产权立法必须从现实的本国国情出发,在充分考量国际条件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量体裁衣,设计既符合现阶段诸方面实际情况,便于与国际交往,又利于未来发展的制度。这既非片面地强调国情,不顾国际大势,也非不顾国情,一味地强调全球化、一体化所能奏效。所以,事情难就难在这里。
在谈到治学之路时,刘教授说,学术研究关键是要讲究方法。方法需要系统地学习掌握,要有秩序、有伦次,零敲碎打、支离破碎、捉襟见肘,是形不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意味着没有学术能力。
“满天星斗不如一轮红日”
“即使有满天星斗,照样是漆黑一夜,只要有一轮红日就足以照亮全球。在科学问题上,学者的任务是给人太阳的光辉,不是给人月亮和星星,更不是给人以行夜路的灯杆。一盏路灯只能照亮五十米。”
当刘教授缓缓地说出这句话时,记者震撼于其间的哲理深度。
他说,学术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而思想的深度又取决于现代的教育水平。刘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应当是理性教育,不是感性教育。它所教诲于人的应当是一种思考的能力,一种学养和思想的维度与深度。
刘教授说,近些年他间或对高等教育进行思考。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世界一流大学?难道是我们的学生不行吗?他认为,在中国,世界一流的学生是现成的,之所以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在于没有世界一流的教师。
“人文社会学科的很多被推崇的所谓名师,不少人是故事讲得好,而不是传授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有些人所做的,类似填补连阔如等传统艺人留下的空白。没有说书的,民众却需要有点知识含量的精神食粮。通过听故事,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讲故事不是坏事,但这不是高等教育。”刘教授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这种评价标准导向应当改变。
古人早就说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如果只是说书高手,零碎知识的贩卖者,那么中国的知识天空里所呈现的永远只是一些小星星。而我们的民族需要的是科学与艺术上的一轮红日。
刘教授喜欢京剧,尤其推崇“马派”。他自认没资格做票友,爱好而已。空闲时,喜欢唱一段马连良的《淮河营》《借东风》。谈起马连良京剧的巧、俏、率,说到《淮河营》里面的蒯彻之善辩,刘教授讲得手舞足蹈、头头是道。他还喜欢旅游与体育。每次外出,有爬山涉水的机会,他从不放过;还是巴西队的铁杆球迷,痴迷于艺术足球,并因此而死看不上法国队;他崇拜英雄,盛赞米卢、马俊仁;也很喜欢篮球,1.83米的个头,年轻时球打得不错;看篮球就过于追求完美,自从乔丹退役后,对篮球也就没有了多少兴趣。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塑造着他自己,而且也汇聚成了这个时代的涌流。当我们勇敢地担承责任时,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长存和更有意义。
刘春田,在知识产权领域辛勤耕耘几十载,他能沉得下去,认真地为学为人,同时他也不甘沉默,自信地挥洒自己的观点……
来源:《法制日报》2007年8月12日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