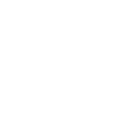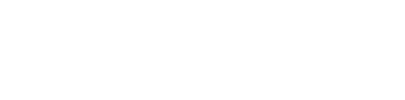


在历史的长河中,《远逝》缓缓展开一幅古色古香的画卷,讲述了一段跨越时代的深情与秘密。故事始于太元十八年的荆州,主人公张玄、刘子骥与薛勉的命运交织,如同江面上轻轻荡漾的波纹,隐含着未解之谜与深远的情愫。一边是古风浓郁的侦探小说风格,将读者带回1938年的湘江,那时的船只与烟雾,不仅是背景,更是命运的隐喻。吴准月,一位生于20年代的女子,她的故事与薛勉的纠葛,映射出家族的变迁与个人的抉择。
《远逝》不仅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情感之旅,也是对过去岁月的深切怀念。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家庭的兴衰,以及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我与真爱的旅程。旅馆“吴氏旅馆”成为故事的纽带,见证了家族的苦难与荣耀,以及两代人之间不可磨灭的情感纽带。在这部作品中,既有历史的厚重,也不乏人性的光辉,让人在阅读中既能感受到时代的沧桑,又能体会到那份纯真的情感之美。一场关于爱、牺牲与传承的叙事,等待着每一位读者的探索与共鸣。

推荐指数:10分
《远逝》在线阅读全文
张玄刘子骥薛勉是著名作者佚名小说作品里面的男女主角,这部小说文笔有保证,基本不会给读者喂毒,是作者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古言小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 太元十八年,行往荆州,赴子骥约。 今日已是离开江州的第七日。 听闻黑鸟鸣叫,抬头寻之,望落日如琥珀般,被西方云霞包裹。 远处有一渔人着衫子与巾幍,袒露胸膛,不畏凉风,于江滩破朽木舟之上躺卧,持杯独饮。《远逝》 第2章 免费试读《烧》上 | 1
姐姐与薛勉的事,该是要从那篇仿古笔调的侦探小说讲起的。 1938年春天,湘江上的船日日夜夜地过。大船都是各家公司的铁壳子汽轮船,烟囱冒烟,有时会发出响亮的鸣笛来。不那么大的船呢,就是私人的木帆船和筏子,用来运点散货,或捕鱼、渡江…… 那天吃晚饭的时间,父亲同我们姊妹讲他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祖父,是在湘江还没有铁壳子汽轮船的时候,搬到长沙来的。 姐姐便顺口算了算,说那该要早过1895年,是马关条约之前的事了。 父亲并非读书人,对于那些事本来不太清楚的。可是既然姐姐那么说,他也就停下筷子想了想,称:“是的,是的。” 父亲大半辈子,一心一意都扑在了旅馆上,不太关心外面的事。但因为母亲在世时是读书人的缘故,受到了一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他是非常支持我们姊妹去读书的。 依我们家的情况,本是供不起两个女孩子读书的,所以父亲总是很辛苦。 父亲讲他的父亲,我们那未能谋面的祖父刚过来长沙的时候,是在江边做纤夫的工作。靠卖命的辛苦和节衣缩食,才攒了些辛苦钱,在江边开了这家旅馆,当时叫“吴氏旅馆”。 旅馆有了些收入,祖父年近四十娶了妻,生了父亲这个独子。 父亲常讲,我们家的命运是算不上很好的。他十七岁那年,祖父便去世了,又过了两年,祖母也离开了他,他只好独自继承下来这家旅馆。 后来,父亲娶了我们的母亲,生下了我们两个小孩。 姐姐是1920年生的,名叫吴准月。他们过了一年多又生下了我,起了个和姐姐只有一字之差的名字吴准星。此后,父亲便从我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来,将“吴氏旅馆”改名为了“月星旅馆”。 父亲常说,命再不好,我和姐姐都是上天给他最好的恩赐。 但父亲也说,从旅馆改名的那一年开始,生意便开始很不好了。因为长沙开埠之后,不同国家的洋人都跑来长沙开旅馆。洋人们有钱,旅馆修得很好,竞争力很强,抢占了很多本地人的生意。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是不满足的,后来不少外国人开始挂着旅馆名头,在明里暗里做着妓院和鸦…
姐姐与薛勉的事,该是要从那篇仿古笔调的侦探小说讲起的。
1938 年春天,湘江上的船日日夜夜地过。大船都是各家公司的铁壳子汽轮船,烟囱冒烟,有时会发出响亮的鸣笛来。不那么大的船呢,就是私人的木帆船和筏子,用来运点散货,或捕鱼、渡江……
那天吃晚饭的时间,父亲同我们姊妹讲他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祖父,是在湘江还没有铁壳子汽轮船的时候,搬到长沙来的。
姐姐便顺口算了算,说那该要早过 1895 年,是马关条约之前的事了。
父亲并非读书人,对于那些事本来不太清楚的。可是既然姐姐那么说,他也就停下筷子想了想,称:“是的,是的。”
父亲大半辈子,一心一意都扑在了旅馆上,不太关心外面的事。但因为母亲在世时是读书人的缘故,受到了一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他是非常支持我们姊妹去读书的。
依我们家的情况,本是供不起两个女孩子读书的,所以父亲总是很辛苦。
父亲讲他的父亲,我们那未能谋面的祖父刚过来长沙的时候,是在江边做纤夫的工作。靠卖命的辛苦和节衣缩食,才攒了些辛苦钱,在江边开了这家旅馆,当时叫“吴氏旅馆”。
旅馆有了些收入,祖父年近四十娶了妻,生了父亲这个独子。
父亲常讲,我们家的命运是算不上很好的。他十七岁那年,祖父便去世了,又过了两年,祖母也离开了他,他只好独自继承下来这家旅馆。
后来,父亲娶了我们的母亲,生下了我们两个小孩。
姐姐是 1920 年生的,名叫吴准月。他们过了一年多又生下了我,起了个和姐姐只有一字之差的名字吴准星。此后,父亲便从我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来,将“吴氏旅馆”改名为了“月星旅馆”。
父亲常说,命再不好,我和姐姐都是上天给他最好的恩赐。
但父亲也说,从旅馆改名的那一年开始,生意便开始很不好了。因为长沙开埠长沙开埠:1904 年,长沙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后,不同国家的洋人都跑来长沙开旅馆。洋人们有钱,旅馆修得很好,竞争力很强,抢占了很多本地人的生意。但即便如此,他们仍是不满足的,后来不少外国人开始挂着旅馆名头,在明里暗里做着妓院和***生意,去赚更多钱。
即使没读过什么书,父亲也知道那些事不好,做不得。在月星旅馆,***和嫖妓都是不被准许的。
月星旅馆的生意和口碑,全靠父亲的辛苦殷勤挣来。买菜做饭、勤洗床品、烧水备茶、值班守夜……他用成倍的付出,让旅馆坚持到了今天。
除了经营,父亲便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了。或许也曾是有的,只是他自我舍弃了。父亲不抽烟、喝酒,也不打牌,攒下来的钱全供我和姐姐去读书。
让我们姊妹都读书是母亲的遗愿,父亲毕生都在小心呵护着。
抗日战争是 1937 年开始的,战争让很多逃难的人从北方来到南方。要住旅馆的人一多,我家生意也好了不少,不然家里是没有钱供我读书的。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你的丁点幸运,可能都是由无数人的不幸阴差阳错给予的。你尝到的每一口小甜头的背后,都是那么浓烈的苦难。
这年我考上大学,和姐姐读了同一所学校。
姐姐比我高一年级,在她入学的时候,那学校还叫“省立的湖南大学”。等到我入学以后,皮宗石先生成了我们新的校长,学校也上升成了“国立湖南大学”,同学们都很高兴。
新校长一来,也给学校带来了新风气。
姐姐前不久写了篇名为《桃花源考》的侦探小说,是用仿古笔调,讲述两晋时期陶渊明与桃花源的故事,在校报上做了三期连载。
听消息灵通的同学说,校报的编辑王老师起初是不愿意登出这篇小说的。王老师认为姐姐的《桃花源考》写得不够严肃,有些许对古人不敬的意味。但那天皮宗石先生碰巧看到了办公桌上的投稿,很仔细地读完了。皮校长认为姐姐的这篇小说写得颇有意思,于是它便在校报上登出了。
《桃花源考》这篇侦探小说一经刊登,便在校内师生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人称赞姐姐的才华和知识,也有人批评她。
那些批评的人喜欢说,这种表达形式太过玩世不恭了。既要用仿古的笔调,那应该是工整严肃的,不该拿来写这么消遣的东西;又或者,妄自揣测古代的先贤,多少是不合适的。
对于这些评价,姐姐倒也不很在意,只说小说创造出来就是要让人评论的,说好说歹,都是一种激励。
关于姐姐的小说登上了校报这件事,父亲很是开心。他原本就认为,姐姐是继承了母亲聪慧多一点的,于是这似乎又暗暗印证了他的看法。
虽说父亲对我们姊妹都挺好,但我知道他是更偏爱姐姐一些的。
知道归知道,我并不对这种偏爱抱有什么怨气。
姐姐真的是像月亮一样温柔而又明亮的人,对父亲如此,对我也如此,她是值得被偏爱的。
那天晚饭,父亲乐呵呵地劝姐姐多吃一点鸡。他假意责备完姐姐总爱吃菜,不爱吃肉,号召她向我学习,又劝我们快点吃。说:“今天夜饭做晚了些,吃太慢,可就赶不上最后一班渡船咯。”
读书的时候,我和姐姐都是在河西学校的宿舍里住的。到了周末,我们便坐渡轮回到河东的旅馆去,陪父亲聊天吃饭,帮助他洗点被单床褥,或者做一些别的家务。
只要是像那时的春天,气候宜人,湘江上可是很热闹的。
学校放了假,女学生们喜欢提着篮子去野餐,坐在筏子上一边吹口琴一边唱歌,唱得是很好听的。在朱张渡中间是水陆洲和牛头洲,日光好的时候,学生们也喜欢去上面春游。
听父亲说,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得时候,上面新修了很多洋行和专供外国人度假的地方。学校老师也讲,那上面曾经有叫个万国球坪的地方,还立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这些屈辱离当年的我们并不久远,幸而那时大家都知道要反抗了。
从东岸的“文津”,到西边的“道岸”,我们这些学生在朱张渡间往返,就和当年“朱张会讲”时,求学问道的那些学子一样,渴求着知识带给我们进步。
但实际上,在我们那个年代,谁也不知道这课还能上多久。
北方的战争越打越烈,消息也不是那么好。
报纸上说日本兵越来越往南边来,可能都要打到湖北了。我们的学校也准备暂时搬到更南边,或者更西边的地方去躲避战乱。
在吃完晚饭,回学校的渡船上,我同姐姐商量,如果学校要搬到那么远的地方,父亲一个人留在这边,可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父亲一定不会放下他的旅馆。
姐姐说:“到时候的事情,到时候再说。”
她这话像是安慰我似的。其实我看得出来,她的表情也十分惆怅。
有这些忧虑的,当然不止我和姐姐。很多同学也都因为日军的日渐逼近而感到焦灼。很多人甚至越来越想不明白,国家都已经成这样了,我们怎么还能安心读书呢?他们想上到前线去,击退那些来犯的敌人。
那天回校的同一班渡船上,就有拿着报纸的男同学,沉沉叹了几口气。
也不知道他看了什么样的新闻。
姐姐用手肘戳了戳我的腰,拉着我起身走,说渡船已经靠岸了。
出了渡口,总要走一阵才到学校。校门口聚了不少同学,在公告栏的前面看热闹。有姐姐的同学见了我们,便走来同姐姐悄声说,“公告栏上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你,快去看看吧。”
我和姐姐走到公告栏前,只见有人用飞舞张扬的毛笔字写着《我读吴准月同学〈桃花源考〉一文》,于是我和姐姐都想看看,他到底是批评了些什么。
我只匆匆看清楚一些段落,以及署名是个叫“薛勉”的人,姐姐却看得极快。
她转身领着我向宿舍楼的方向走。我知道她已经看完了,就问她:“这人写了些什么烂东西?”
“不能说人家讲得不对,是我自己没把那小说写得更清楚些的。”
姐姐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心里有什么委屈,是不愿意多说的。
我只感觉到,她紧紧攥着我的手,不时会传来轻微的颤抖。
她没有意识到都把我攥疼了,而我也不说,就让她那样攥着,领着我走。
我们走着走着天就更黑了,那晚只有大大的月亮挂在头顶,发出很白的光,却见不到什么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