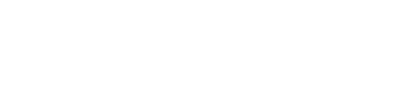


最近儿女有权为老人作出重大医事抉择吗_一个社会学家会如何谈论死亡事件在热度非常高,为大家准备了完整关于儿女有权为老人作出重大医事抉择吗_一个社会学家会如何谈论死亡事件的所有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这方面的情况,请持续关注本站!

对于如何庄重且有尊严地离世这一终极议题,景军提出了三个核心要素:缓解疼痛、情绪稳定以及尊重个体的自主权与决定权。然而,他进一步强调,我们真正需要构建的是一个健康、公正且富有协商精神的医疗社会环境。
这篇文章源自景军的讲述并由砂仁撰写和紫砂编辑。在中国,每年约有1000万人离世,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000万个家庭经历生死离别。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景军专注于医学人类学和健康人类学研究,受此统计数据触动,决定开展对中国人死亡状况的系统性研究。自2019年起,他的团队招募了百余名青年学生和十多位教授,分别进行了实地调研和访谈,收集了家属对亲人去世过程的叙述,以及医护人员、社工及医务志愿者在临终关怀工作中所经历的故事。在中国进行此类研究极为困难,研究者难以直接观察死亡现象,于是团队还将自身的经历纳入研究样本。
调研过程中,景军深刻感受到每个离世场景各具特色。例如,他曾陪伴一位70多岁的同事走过最后一程,当时病房简陋冰冷,除了一张床就是急救设备。景军询问家属是否需要换一间有阳光的房间以让病人在最后时刻过得稍微舒服些,但家属坚持留在原医院,尽管条件艰苦,至少有机会争取救治。这使景军不禁思考是否存在一种更人性化的离开方式。
他还探访了一家专做临终关怀的医院,还未进入就闻到混合着多种气味的气息,令他想起了母亲在家中去世时未能得到专业清洁护理、也无法开窗透气的情境。这家医院门口的气味让他意识到,即使是一家致力于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也可能无法保证为临终者提供清新空气,从而质疑其能否提供优质的临终照护。
在调研中,他们搜集的不仅仅是受访者的口述,还包括亲身体验。景军由此联想到,母亲在临终前所在的病房并未充斥那些令人不适的味道,这是否意味着死亡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气味控制之中?
母亲于2021年去世,生前坚持要求出院,不愿独自留在医院。景军深知医院环境对她而言十分熟悉,因此最终将她接回了家。但实际情况是,家庭成员并不具备专业护理知识,尤其是在冬季,门窗紧闭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房间弥漫着异味,全家人都因疲惫不堪而生病。幸亏在好友路桂军大夫的帮助下,母亲得以入住长庚医院的缓和医疗科,那里有宽敞的病房和专业的医护人员,他们专注于减轻病人的疼痛,而不只是简单给予止痛药,还会细致地处理如呼吸机使用、翻身护理等细节问题。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最后的日子,尽管前期历经艰难,但相较于许多人,她的离世已经算得上较为平静。
这次经历加深了景军对于缓和医疗在中国迫切需求的认识。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未经缓和医疗服务的临终病人普遍承受较大程度的疼痛(评分为6-7分),而接受过缓和医疗的病人则显著降低了疼痛水平(评分为2-3分)。这表明临终关怀的确能够显著提升重症患者的临终生活质量。
自2019年以来,景军的团队共收集了364例死亡叙事,揭示了中国家庭在生死关怀与死亡话题禁忌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关于临终病人的病情告知问题。西方国家倾向于由医生根据病人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决定何时及如何告知病情,而在中国,大多数重病患者并不会第一时间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实情,通常是家属首先知道,有时病人直至去世也不知道实情。
这种医疗家庭主义现象在中国医疗体系中普遍存在。从诊断之初,家属便扮演着牵线搭桥的角色,寻找优秀的医生、争取医院床位或是购得廉价药品。在告知病情、重大手术签字等方面,医生也需要征得家属同意,否则即使病人同意,家属仍可能追究法律责任。在中国许多医院,知情同意书竟多达四五十种。事实上,大约70%的临终医疗决策由家人或朋友做出,其中通常由成年子女负责,原因既包括经济因素(如多数照料和费用由子女承担),也包含文化和道德因素(如病人清理工作主要由家属承担)。因此,家属成为病人的一部分,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就医行为在许多家属与病人之间形成了默认共识,即子女有权代表长辈做出重大医疗决策,其中包括隐瞒病情。
然而,这种方式带来了矛盾。景军的研究发现,由老年人自行做出的医疗决定更倾向于选择减轻疼痛的保守疗法或放弃治疗,而子女往往倾向于积极治疗,甚至动用ICU干预,导致许多老年人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即过度治疗问题。研究中发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家属成功说服亲人接受家庭的决策,家庭选择替代了个人意愿;二是严重违背了患者的个人选择,例如一名受访者讲述,他在父亲弥留之际违反父亲遗愿为其插管,而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一直在用手戳他们,仿佛在指责这一决定。
此外,研究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复杂情形:关于病情告知问题。在某些案例中,家属将实情告知临终者,但这可能导致原本无法获取症状控制和注射性麻醉剂的偏远地区患者陷入绝望。景军由此反思,对于即将离世的人来说,是否一定要告知他们真相,以及为何要这么做?若临终者无法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那么将他们即将离世的消息公之于众,岂非残忍至极?
近年来,在临终医疗决策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中国抗癌协会提出的“三方联合预立医疗计划”或称为“生前预嘱”,要求医生、病人和家属共同制定临终医疗方案,涵盖是否放弃呼吸机、心肺复苏术、鼻饲、输血、抗生素等治疗手段,以及器官捐赠和丧葬事宜等。然而,现实中,这一计划仅在深圳等地得到了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推广,实际签署此类文件依然面临重重困难。
在这项研究中,景军特别关注了许多临终者展现出的“反向关怀”意识。以往的临终关怀研究常常将临终者视为被动关怀的接受者,但景军团队在调研中却发现,许多人在生命的终点不仅接受关怀,还会主动关爱家人、医生、病友乃至社会。这种关怀表现在多个层面,如减轻家人精神和经济压力、关心其他病人、倡导简约葬礼和环保安葬等。
景军自2000年开始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一直警惕一种被称为“人口负债说”的言论,该言论认为老年人增加会使青年人口比例减少,加重社会福利压力,与年轻人争夺资源。他认为不应将老人视为消极、无助的形象,而应认识到他们拥有独立主体性。
在开展临终叙事研究期间,景军开设了一门关于死亡的社会学课程,引发了学生们的广泛兴趣和热烈反响。然而,他在课堂上发现,关于死亡话题的讨论相对局限,学生的观点往往单一、表面化,缺乏现实生活经验。课程促使景军思考死亡观的多样性,他认为单一的好坏判断标准在死亡问题上是极其危险的,死亡观是复杂的,应允许多元共存。
在此基础上,景军提出了应对中国当前临终关怀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如结合社区与家庭、医院与家庭的力量,解决照护人手短缺的问题。然而,实际操作起来面临诸多困难,如家庭照护如何计费、医生是否愿意提供上门服务等。此外,现实情况往往比简单的呼吁更为复杂,如中国老年照护观念的变化,既有呼声要求“去家庭化”,减轻中青年照料负担,又有一部分老年人坚守传统的家庭关怀理念,难以接受“去家庭化”。
景军的研究揭示了一系列有效实践案例,如上海实行的医院、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临终关怀制度,解决了子女照护负担和医保问题;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组织学生参与志愿服务,为数千名临终患者提供了护理和心理援助。
然而,这些模式的普及和推广仍面临挑战,主要源于医院经济效益的角度,临终关怀服务被视为低收入科室,使得这类项目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景军自身的经历,如父亲临终前医生坚持要求完成透析后再手术,而家属担忧如此操作风险过大,却又无法改变医生的决定,再次凸显出改善医疗社会生态的根本性紧迫性。
总的来说,无论是希望还是忧虑,景军的研究成果都为我们展现了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及其背后复杂的社会、伦理和文化议题。尊严离世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需要我们在构建一个更健康、公平、包容的医疗社会环境中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标。
以上内容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儿女有权为老人作出重大医事抉择吗_一个社会学家会如何谈论死亡全部信息,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后续或相关内容,请关注多特软件站,持续更新给大家带来最新消息!
了解更多消息请关注收藏我们的网站(news.duote.com)。



